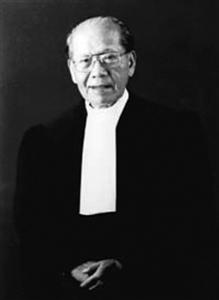


赵理海著作

赵理海(左一)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与同事们合影
赵理海(1916~2000),著名国际法学家。1916年出生于山西闻喜县,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先后获得燕京大学文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1957年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2000年10月10日在北京病逝。他历任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民盟中央法制委副主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海洋学会理事,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学会国际理事会理事,海洋问题研究会副会长等职。1989年,为了推动中国海洋法研究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倡议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海洋法学会改为中国海洋法学会。1996年8月,他当选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赵理海还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据 《中国审判》 报道
1996年8月1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一天,98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缔约国聚集在这里,在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着一场引人注目的选举。这次选举将要产生的,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首批21名法官。这些法官将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 和其他有关文件的要求,从缔约国政府推荐的33名候选人中产生。
选举当天,整个联合国总部都笼罩在一片既严肃又紧张的气氛中。选举从上午开始,一直进行到深夜。经过8轮的无记名投票,21名法官终于产生。国际海洋法的历史上庄严地记下了这21名法官的名字,而他们中间就有一位中国人,他就是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赵理海先生。
这一年,赵先生正好80岁。正如选举结果产生后国内外媒体评价的那样,无论是在个人品格还是在海洋法学识方面,赵理海先生担任海洋法法庭法官一职都是当之无愧的。
他是北京大学里的“先生”
在北京大学一直沿用着一种称呼习惯,大家对那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尊称为“先生”。得到这种称谓的人并不多,但赵理海教授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尊称为“先生”。“赵先生”,这是同事和学生对他共同的称呼。
赵理海先生于1916年7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父母给他取名“理海”。他的一生也真的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赵先生在燕京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和政治系学习,并于1944年在哈佛取得了国际法博士学位。
在哈佛期间,赵先生刻苦攻读,博览群书。他充分利用哈佛图书馆的条件,完成了 《中外旧约与国际法》 的博士论文。论文中表现出的作者的出众才华、深厚的法学功底和超群的分析能力都使得指导他的哈佛教授们赞叹不已。同时,哈佛优越的学习研究环境、深厚的法学底蕴为赵先生日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底,赵先生学成归国,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55年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生涯。
1945年至1947年,赵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后又到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1957年,他来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从此,燕园又多了一位知识渊博的“先生”,学生们又多了一位令他们爱戴的师长。
建国后发表文章配合外交实践
赵先生的学术造诣主要在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方面。
早在1947年,赵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际公法》,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国际法在中国很不普及,国际法的教材也很少,该书就成了当时全国各大学法律系的通用教材。该著作也初步展示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才华。
1949年以前赵先生发表的论文还有:“国际法的展望”(载于 《大陆评论》,1946年第2-3期); “联合国宪章释义”(载于 《世界政治》,1948年第1期) 。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配合我国的外交斗争,维护我国在国际法上的正当权利,赵先生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发表了一些与当时的外交实践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苏伊士运河问题与国际法”(载于 《政法研究》,1957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领海主权的正义斗争”(载于 《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古巴问题与国际法”(载于 《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4日) 。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的原因赵先生几乎没有发表著作。
“文革”期间用剪报跟踪国际法动向
十年浩劫期间,特殊的环境使得赵先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但他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从1957年开始,他就坚持剪报。即使在牛棚里,他也坚持找 《人民日报》 跟踪国际法发展的动向。赵先生曾经说“困难、阻挠、讽刺、打击、迫害,可曾改变我坚定不移地要搞科研的信心和决心?没有,丝毫没有。”
正是在“五七干校”的这段时间里,赵先生凭着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海洋法发展的前景,将海洋法确定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干校生活刚一结束,他回到北京便立即投入到海洋法的研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便将全部的生命与热情都投入到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改革开放后迎来研究高峰
1982年和1984年,赵先生利用他在干校积累的资料,先后出版了两部著作: 《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 和 《海洋法的新发展》。其中 《海洋法的新发展》 是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诞生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该书在国内是第一部论述新海洋法公约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为数不多的同类著作之一。
该书的出版在世界国际法学界引起了注意,著名的 《美国国际法杂志》 还专门作了书评。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赵先生在海洋法领域的研究已走在了中国和世界的前列,也标志着赵先生学术研究的高峰时期已经到来。
从1979年开始,赵先生发表了大量论文。仅八十年代他就发表了20篇论文,主编了两部著作——《国际法论集》(法学杂志社,1982年)和 《当代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87年)。其内容涉及国际法诸多领域里的问题: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主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否决权、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等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赵先生一直笔耕不辍。1996年,他在80岁高龄时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海洋法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担任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之后,他先后在 《中外法学》 上发表了5篇论文,介绍和分析法庭及法庭受理的案件。在他去世的2000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渔轮“卡莫柯号”案》 发表在2000年 《中外法学》 第4期上。
应该指出的是,与法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国际法学的研究是有其特殊性的。由于国际法的研究参考资料几乎都是外文的,这就给母语是汉语的中国学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国际法学者的著述一般较研究国内法的学者要少,但赵先生是国际法学界为数不多的几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之一。
赵先生在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领域的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使得他在国内外法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他是学者也是战士
他是学者,也是战士,他用手中的笔,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斗争,用他娴熟的国际法知识维护国家的权利。他的论文和著作许多是为了维护我国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权利而写的。其中有:维护我国领海主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领海主权的正义斗争》;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有 《从国际法看香港问题》、 《澳门问题的由来》; 在中印领土问题上有“非法的 ‘麦克马洪线’”。赵先生的这些文章往往从国际法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的合法主张,强有力地批驳了对方的观点。
《日本法院对光华寮的审判严重违反国际法》 是赵先生的论文中最具代表性的,该文发表在 《人民日报》 上。
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86年作出错误判决,将原本属于中国的光华寮(一所建筑物)判归台湾所有;1987年,大阪高等法院维持上述错误判决。这是一个严重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益的判决。赵先生立即在《人民日报》 上撰文进行批驳。他还应光华寮案上告人辩护律师团的要求,对该案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以个人名义提出了长达万言的意见书。意见书中他以大量法律依据有力地论证了日本地方法院的判决是违反国际法的。赵先生的这份法律意见书得到了日本律师的赞叹。
今天研究东海大陆架问题时,必须要参考的两篇文章仍然是赵先生写的“从 ‘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 看东海大陆架问题”和“适用于东海大陆架划界的法律原则”。
在这两篇文章中,赵先生详细论述了国际海洋法中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分析了国际法院的有关案例,用大量的证据论证了东海大陆架划界应适用的原则。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读赵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仍会发现它们的闪光之处。
在南海问题上,赵先生在1992年和1994年分别写下了《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和 《关于南海诸岛的若干法律问题》 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学者此类文章中最重要的两篇,其中阐述的观点,如“发现”和领土取得的关系、“禁止反言”、“时际法”原则仍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