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来海大做讲座

本站讯 “把人生踏上40之途,称作进入不惑之年,这种儒雅的说法,典故出于《论语》。但是,它充其量是对夫子自道断章取义的结果,而决非是对经典含义的确切运用。”2010年9月26日下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为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中心组(扩大)做题为“解惑”的专题讲座。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于志刚,党委副书记李耀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贵聚,校长助理、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陈锐,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光志等聆听了讲座。
陈少明教授的讲座共分惑与不惑、惑的多样性、智者不惑、一个惑者四个部分。首先从孔子“不惑” 的提法入手,尝试把“惑”作为普遍的人类精神现象进行探讨。在区分惑与无知,惑与怀疑的不同意识特征之后,作者对惑的多样性作分类描述。在此基础上,把孔子与庄子当作有助于解惑的两类不同的经典思想资源加以评介,并以王国维为例,讨论其惑所包含的心理与时代因素。
在“惑与不惑”的讲解中,陈少明教授指出,惑是一种古老的精神现象,虽然古代文献中对惑的含义作专门讨论者很罕见,但关于“惑”一词的使用在秦汉间则很平常。虽说“知者不惑”,但“惑”决非一般意义的无知。因为疑惑者并非不知道对象的表现,也不是不知道对人的行为的一般评价尺度,故不是无知。惑不是怀疑,怀疑就是不相信或不信任,但不是任意的否定或拒绝,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或信念的基础之上。疑是比惑更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
陈少明教授说,对“惑的多样性”的划分是尝试性的,因为惑几乎涵盖人类意识的所有领域,从普通日常经验,到复杂的知识与精神生活,难以穷尽。日常经验的惑、理智领域的惑,都是认知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可通过经验科学的发展慢慢加以解决,或者会由哲学家们自己进行理智的补救。但它们与人类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其实无多大关系,真正困扰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是价值上的惑,包括情感的、道德的、以及信仰问题上的惑。孔夫子“四十而不惑” 所指的那个“惑”,应是人在价值领域上的惑。
“智者不惑”,不惑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但声称有此境界者,大概只有孔夫子。陈少明教授指出,“四十不惑”,不是指孔子变得神通广大。而是他以坚定的精神信念为前提,有更丰富的处理复杂道德难题的经验。庄子是另一类型的智者,对惑从形而上的层次上予以思考。庄子、孔子惑与不惑的对比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自我的确定性,一是对生死的态度。
惑是人生的经验,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面对同样的惑。有些惑则可能是某些时代特有的现象,更有些只是少数人才会体验到的难题。陈少明教授说,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一个惑者”。惑的问题有个人的,也有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人的惑中,有不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那是人性的根本问题。但也有某一时期的人才感受到的,那就是时代的问题。人生之惑与时代之惑不一样。而个人之惑中,有些是偶然的异常的,有些则可能本来是普遍的,但只有敏感者才被困住。王国维几乎是集所有类型的困惑于一身的人,所以他发出“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的慨叹。
陈少明教授说,解惑之解,含义可有三解:解决、解释与解脱。涉及认知之惑,原则上通过发展人类的认知能力,由解释而得解决。面对价值之惑则有分别,在日常道德实践中,如孔子所示范的,多数通过权的方式来处理,争取把副作用控制在最低的程度。至于自觉不能解而又非面对不可的事情,常人常会采取转移目标的方式,实际上是变相的逃避。不过那只是问题不严重情况下才有效。只有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者,才需从根本上寻求解脱之道。彻底的解脱,是宗教的皈依,以及自杀。就此极端状态而言,接受庄子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代替方式。所以,尽管思想的路数大不相同,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庄子,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精神价值,依然是简朴的道理——热爱人生。
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中心组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各院(系)院长(主任),学校管理干部聆听讲座。
文/图:冯文波

讲座现场
附:陈少明教授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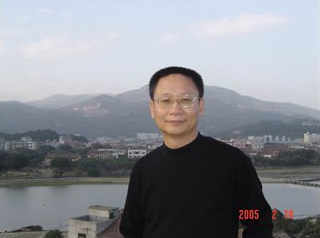
陈少明,男,1958年生,广东汕头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曾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作访问研究员(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2年3月 至8月)。学术兴趣集中在中国哲学、人文科学方法论两个领域,近期致力于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的研究。为哲学系本科生讲授《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 频道推荐
- 最新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