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汐人生 德教双馨—记我国著名潮汐学家陈宗镛先生
陈宗镛先生身材不高,极瘦,也许是从小在海边长大,也许是长年与海打交道,海风给了他黧黑的烙印。每天,他戴着眼镜,推一辆旧自行车去学校上班。他给人的印象是文弱的,毫不起眼的。可是,谁能想到,他有那么惊人的毅力,那么坚定的事业心,那么坚强的一副硬骨头。谁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文弱书生,领军统一了全国高程基准,创造了海平面研究和潮汐学领域的一个个国内第一、世界领先,成为世界著名的潮汐学专家、我国海平面变化研究和海洋潮汐学的奠基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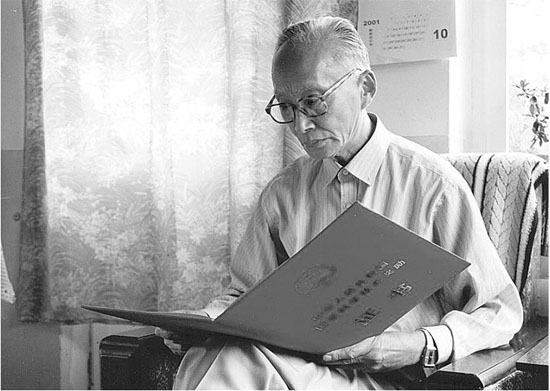
自古才俊多磨难
1928年,陈宗镛生于福建省诏安县甲州村的一个渔民世家。甲州村是一个渔村,地处东溪下游,东西两条溪流环抱,南面濒临宫口港,是淡水、咸水交汇的地方,因盛产鱼虾,以讨海而闻名遐迩。每逢农历大潮时,风浪澎湃,烟波浩淼,赶海人络绎不绝。据县志记载,明朝以前,这里是诏安湾畔宫口湾内的一个岛屿。随着岁月流逝,上游的泥沙淤积,现在已与大陆接壤了。在这个半岛上,礁石因受潮水冲刷侵蚀而变得千姿百态、光怪陆离,海涛湍急的“相杯石”、水波荡漾的“莲花石”……应有尽有,波光帆影、风景绮丽的古迹“临江亭”就修建在这里。
然而,当陈宗镛降生到这个美丽富饶的小渔村时,迎接他的并不是玫瑰花般的艳丽色彩。3岁时父亲出海不幸遇难,是母亲忍辱负重、靠编织渔网把他拉扯大。天寒地冻的冬天,母亲用手蘸着彻骨的凉水织网……24岁就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用生命呵护着这个孤儿,不到40岁便满头白发。
伴随着潮涨潮落,每天都在海水里浸泡的陈宗镛一天天长大了、懂事了。他渴望了解为什么大海那么无情地夺去父亲的生命;为什么涨潮了,大人们就纷纷驾船出海,满载而归;落潮了,人们就急急拥向海滩,去挖海蛎子、摸鱼虾、捉蟹子,采拾种种海鲜。海潮的神秘感不仅为这个大海的儿子带来了无尽的好奇和敬畏,更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之路。
陈宗镛的初小阶段,就在本村就读,高小时转学到离村不远的后园村小学。懂事的陈宗镛深知母亲的艰辛,立志学出成绩报答母亲。当时诏安县全县的最高学府就是一所初中,陈宗镛是全县500多名应试考生中的第二名。因学习刻苦,加之生活艰难营养跟不上,入学体检时的他体重仅24.5公斤。
考入初中后,正是“逃鬼子”的兵荒马乱时期,学校为躲避白天日本飞机的轰炸,只好利用早上和傍晚时间上“疏散课”。
在外祖母及舅舅们的资助、关照下,他得以在战乱纷纷中读完高中。
1948年,带着儿时的梦想,陈宗镛如愿以偿地考入厦门大学海洋系,踏上了探索海洋奥秘的征程。这年寒假他乘船回家,船中途触礁,说来也巧,当时正遇涨潮,船被潮水推上浅滩,他们被搭救上岸。这使他又一次感受到潮汐的力量和它对人类的重要性,从而更加如饥似渴地扑向知识的海洋,几近“贪婪”地索取海洋知识。在著名海洋学家唐世凤教授的指导下,他完成了毕业论文《潮汐分析》。
1952年,陈宗镛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当助教,适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海洋系并入当时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他跟随唐世凤教授带着两届学生来到了青岛。
著名海洋学家赫崇本教授卓有远见地把动力海洋学粗分为流、浪、潮三个分支,并培养他从事潮汐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此,陈宗镛的一生便与潮汐学和海平面变化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经风雨露峥嵘
在海洋科学界前辈和老师赫崇本、唐世凤、毛汉礼等教授的指导下,陈宗镛在潮汐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进步很快,逐渐展示出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海洋学者的不凡才华。他的学生周天华深深地爱上了他,通过教与学的纽带,在向海洋科学进军的征程上,他们结为最亲密的伴侣和战友。
正当陈宗镛意气风发、扬帆起航时,灾难降临了。195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潮使他和许多正直有为的知识分子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打蒙”了。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崂山修水库。当时,一对对“右派”夫妇分道扬镳,而年轻的周天华却冒着“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多次到改造营地看望他,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气。他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地“改造”着,直到有一天传过话来,“已经改造好了,可以上讲台了”。
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穷困、精神上的压抑,使本来身体就瘦弱的陈宗镛百病缠身:胸膜炎、肝硬化、胃病、肺结核、神经衰弱等接踵而来。但他没有向厄运低头,依然勤勤恳恳地教书、偷偷摸摸地研究,身处逆境而不气馁。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所谓“有问题的人”取得的任何成果,是不会被人承认的,而且往往还会制造出一些人为的障碍。有些资料,被莫名其妙地加以封锁,教潮汐、研究潮汐的人偏偏不准看潮汐资料,当然更不准用潮汐资料去开展科学研究了。陈宗镛不敢奢望,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和勤奋,坚定执著地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一分成绩需要千万滴汗珠的浇灌。1959年夏,陈宗镛引入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杜德森方法,设计出31张表格和9片镂孔格,每天十几个小时挥汗如雨地用手摇计算机连续摇了60多天,在我国首次作出一年潮汐观测资料的分析,求出61个分潮的调和常数,并作出准确预报,使当时的潮汐预报达到了国际水平,被海军和有关海洋部门采用。至今,一年资料的潮汐分析和预报仍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
1960年,陈宗镛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陈宗镛公式”的计算日平均海平面的低通数值滤波公式,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计算日平均海平面最简便的公式。经与19年每小时资料计算结果对比,表明其准确度和已有的国内外4种公式相近,都准确到毫米量级。
1965年,陈宗镛开创了含摩擦效应的泰勒问题研究,比西方同类研究早10年。这一年他还综述了潮波数值计算的原理和方法,该论题从海区到大洋延续半个世纪,一直是海洋潮汐研究的重点内容,特别是随着卫星高度计的采用,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
“文革”期间,陈宗镛3次应邀到浙江温州参加鸥江海涂开发和航道整治研究工作。除了白天正常观测外,为了保证测量数据准确可靠,他不顾当时“武斗”子弹横飞以及江水湍急稍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险的险恶环境,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晚上都要乘船在沿江13个潮位站逐个检查,表现出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大无畏胆识和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
“文革”中,揪斗批判、隔离审查、劳动改造等更是频频光顾陈宗镛。他出门接受批判,回家钻研海平面和潮汐。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严冬总会过去,党、国家和人民需要科学。是海平面和潮汐支撑着他,顶住了一次次狂潮和恶浪的袭击,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扑进科学的春天
1976年,因国家建设需求,全国一等水准布测会议提出了重新确定我国高程基准的研究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作为主要承办单位,立即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大连、天津等地拜师选将,招贤纳才,经过3个多月的奔波调研,依据参照许多单位和专家推荐,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完成重新确定我国高程基准的研究任务,陈宗镛是最佳人选。
正当部队的同志兴冲冲地来找陈宗镛时,有人“正告”他们:“陈宗镛是右派,我们可把话说在头里!”
部队同志不理这一套。
知遇之恩当全心相报。陈宗镛迅速进入角色,以科学家的严谨制订了长达十年的研究计划,并身先士卒,躬行垂范,立即收集和编写相关资料。10年,他斗室里的灯火常常是彻夜不熄;10年,他由46岁进入56岁,将人生最壮美的华彩乐章奉献给了“中国海拔”。而陈宗镛与部队高工汤恩祥的合作友谊犹如陈年老酒,弥久弥香,历经30多年,至今仍在合作开展研究工作。
为了给部队同志讲解研究必备的相关知识,陈宗镛在当时连打字机都没有的情况下,复写讲义。为了提高效率,他一次复写5份,每一份几十页,手都写肿了,之后一个多月胳臂抬不起来,手里拿不牢东西。
从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到广西白龙尾沿海,部队和地方的科研工作者以及上百名测绘战士几十米、几十米地一步步硬是量了一遍。
就是靠这种拼搏精神,陈宗镛和汤恩祥等人踏遍祖国万里海疆,历时10年,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了42个验潮站累计1000多站年的观测资料。经过联测,首次获得了20245个固定水准点的精确高程值,控制并统一了全国高程基准。
1986年9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比1956年黄海平均海面稳定精确,科学实用(这次研究发现1956年黄海平均海面有300多处原始资料有误———笔者注)。国家一等水准网的布设规模和实际精度均达国际水平”,并被正式命名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
1987年5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测绘局向全国公告,启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统一的高程基准,成为我国测绘、制图、防洪、防潮、地壳升降监测等都必须采用的高程基准。
是科学的春天,使陈宗镛走进了收获的季节。
1980年,陈宗镛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潮汐学专著《潮汐学》。“该书是我国潮汐学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论述严格,内容亦较丰富和全面”,我国海洋科学奠基人之一毛汉礼先生如是说;“陈为国际海洋潮汐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海洋潮汐工作组主要成员斯德威切斯基(美国)亦给予高度评价。
1991年,他和同事们完成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海流数值预报表(渤黄东海及西北太平洋)》的研究报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国家专家组鉴定后认为。
对于潮汐分析预报模型,陈宗镛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由杜德森的11对订正公式发展成58对订正公式,理论上更加严谨,预报精度也进一步提高,为我国大量船舰提供了可靠的潮汐预报表。
1985年以后,陈宗镛带领研究人员除继续收集50多个验潮站的资料外,又收集了全球共500站12000站年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首次在国内提出“海平面并非平面”,而是“南高北低,相差70(±10)厘米”。根据这一沿海平面空间变化,汤恩祥发现了全国一等水准测量中的问题:天津至北京、至柳桥(山东)、至绥中(辽宁)三条路线的重大错误(天津至北京差了12.85厘米;天津至柳桥差了13.81厘米;天津至绥中差了26.23厘米)。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进行了重测,确认属实,使其及时得以纠正,避免了对测绘及其应用上给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研究,特别是京、津、唐地区的建设造成损失。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随机动态分析、预报模型等5种平均海平面分析预报模型,并求得了均衡基准下的中国沿岸平均海面变化速率和全球平均海面变化速率。海平面变化研究成果的鉴定结论和查新报告称,“成果在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随机动态预测模型居国际领先地位”。
此后,一系列科技成果奖项纷至沓来:
1988年,“1985国家高程基准和用流体动力水准联测海南岛高程的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列第一位),《潮汐学》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独著);
1989年,“潮汐潮流的分析和预报”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列第三位);
1991年,“海流数值预报表(渤、黄、东海及西北太平洋)”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列第三位);
1993年,“搞好课程评估,确保教学质量”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列第二位);
1994年,“中国器测海面和沿岸地壳形变的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列第一位)。
世纪之交的2000年,陈宗镛更是喜讯频传:
“中国沿岸现代海平面变化及其应用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列第一名);
“中国沿海月均和年均相对海面的机理和预报的研究”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列第一名)。
这是一位老海洋科学家向新世纪献上的一份厚礼,这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跟党坚定前进半个多世纪的世纪总结。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的奉献,1988年至1995年,陈宗镛先后两次被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共山东省委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0年起,终生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艰苦卓绝做痴人”
20世纪40年代的厦门大学久负东南民主堡垒盛名,陈宗镛在此就读期间,就曾被选为厦大学生会副主席、理学院学生会主席。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热血沸腾地与同学们一道配合解放军南下,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发起最后攻势。
陈宗镛向往共产党,为党的壮丽事业贡献一生早就是他的夙愿。无论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还是“文革”10年动乱,他心中的航标灯一刻也没有熄灭,对党的向往一刻也没有动摇,因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共产党。“大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我历经坎坷,但我深切感到是党给了我新生。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时如是说。
1986年1月4日,是进入花甲之年的陈宗镛先生终生难忘的一天,经过近40年的不懈追求,他终于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这一年成了陈宗镛先生人生新的起点。他精神焕发,干劲倍增,仿佛年轻了许多。
这一年,他担任了高教研究室主任,在搞好自己的潮汐研究的同时,承担起全校的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陈宗镛忘我地工作着。2000年3月,老伴、也是自己科研的战友和助手周天华教授因病去世,他含泪送走老伴,回来又扎进书房埋头科研。他知道老伴在默默看着他、鼓励他,希望他能挑起两人的重担,为党、为国家多作贡献。
2001年2月。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属于科学。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向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获奖人员和集体颁奖。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出席大会,并与获奖代表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合影时,73岁的陈宗镛先生被安排在400多名获奖代表的第一排,他的两眼湿润了,半个世纪的潮汐人生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有多少心里话要向总书记说,要向党汇报啊……
2002年7月,陈宗镛先生以一名老科学家、共产党员的身份,荣获全国“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金杯奖,再赴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进入80华诞的陈宗镛先生每天仍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他的潮汐学,胸装四海,精神矍铄,伏案著书,指导后生。最近,他又出版了凝聚着大半生心血的《潮汐与海平面变化研究陈宗镛研究文选》。“从这本文选可以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陈先生在培养人才和海洋潮汐、现代海平面变化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创新性成果,也为我们继往开来、进一步提高潮汐和海平面的研究水平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国洪语)
陈宗镛先生笑谈自己的一生是“惊涛骇浪犹奉献,艰苦卓绝做痴人”。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痴”就是对教书育人和潮汐科学的研究如醉如痴,而自己则是朝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目标不断地攀登着。
正如他的一位学生写的诗“献身海洋六十年,弄潮敢为天下先。标定零点泽后世,驾驭潮汐一圣贤。”道出了人们对陈先生景仰的心声。














